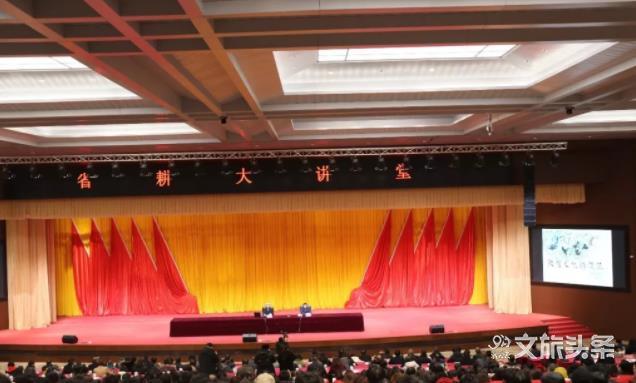
12月8号,昭通市举行“省耕大讲堂”专题讲座。敦煌研究院党委副书记、院长、学术委员会主任委员赵声良应邀就《敦煌文化的价值》作了专题讲座。

讲座中,赵声良以其广博的知识和生动的语言,从历史和现实的高度,通过详实的数据和实例,精彩生动地讲述了敦煌文化辉煌璀璨的悠久历史和成效卓著的保护、传承、发展历程,深入浅出地阐释了敦煌文化不可估量的世界文化艺术价值,给大家带来了一场丰盛的文化盛宴,让大家更直观、更直接、更深刻地感受了敦煌文化的深邃与久远、博大与精深、辉煌与灿烂,对于大家进一步深刻认识和把握中华文化,更加增强文化自觉,坚定文化自信,深入推进昭通历史文化的保护、传承和发展具有重要的指导意义。

昭通学院学生梁佑群:"通过今天的这个讲座,我对敦煌文化也有了不同的理解。我认为敦煌文化在河西走廊是一颗闪烁的明珠。我们也知道敦煌莫高窟也称为千佛窟,它的那个“千”也代表永恒的意思。我觉得在这个意义上来说,也说明了敦煌文化它的价值是非常大的,应该让它永恒的发扬下去。"

昭通学院学生刘欢:"千年莫高,人类敦煌,它有很多年的历史。今天听了赵老师的讲座,我从他的各个方面还是学到了很多。"

昭通学院美术与设计学院院长、教授秦明华:"今天听了赵院长的讲座,对传统文化这一块深有感受。从敦煌艺术的传承和保护,我就联想到我们昭通在非遗这一块有很多东西。所以我们赵院长这些知名专家,我们可以邀请作为客座教授,对昭通非遗这一块的传承给我们一些指点,把这个文化带到我们学院里面,把非遗的文化和昭通学院的教育结合起来。"

市委副书记、市长郭大进主持讲座。他指出:千年莫高,人类敦煌。敦煌对于世人,是艺术的殿堂,是精神的高地,是心灵的圣域。通过赵院长的精彩讲授,让大家更加深刻地了解了敦煌莫高窟的重大意义,也领会了“坚守大漠、甘于奉献、勇于担当、开拓进取”的“莫高精神”。
昭通“朱提文化”曾繁荣一时,“望帝故里”“汉洗之乡”“水塘坝化石地”“朱提故城遗址”“汉孟孝琚碑”“晋霍承嗣壁画墓”“唐袁滋题记摩崖”等印证着昭通的历史与文明,历史文化、民族文化繁荣兴盛、交相辉映。厚重灿烂的文化滋养着一代又一代的昭通儿女,文脉绵延传承,文化事业欣欣向荣,诞生和哺育了“国学大师”姜亮夫等一大批文学泰斗,形成了备受关注的“昭通作家群”和“昭通文学现象”。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文化是一个国家、一个民族的灵魂。文化兴国运兴,文化强民族强。”作为新时代的昭通,刚才声良院长一再的强调文化的重要性、人才的重要性,这个也是我们将来昭通党委、政府努力的方向。我们四套班子一定会全力以赴的为我们昭通文化的兴盛、为昭通发展人才的培养竭尽全力。我们下一步,要专门研究怎么样支持昭通文化的发展,支持昭通人才的吸引和培养。"

市领导陈真永、赵长胜、晏祥莉、吴静、苏建宏、田渊、段登位、王东锋、杨建军、陶仁,昭通学院院长陈红,昭通学院副院长铁云峰、张毅敏,市政府秘书长郭晓东;曾令云、陈孝宁等部分本土文化名人和退休老干部,以及市直各单位、昭阳区、昭通学院以及企业的代表到场聆听了讲座。
为了进一步帮助和指导昭通做好文化遗产的保护和传承工作,推动昭通文化事业繁荣发展,助力昭通脱贫攻坚和经济社会高质量跨越式发展,应昭通市人民政府和昭通学院的邀请,赵声良担任了“昭通市文化顾问”和“昭通学院学术委员会委员”,郭大进、陈红分别代表昭通市人民政府、昭通学院为赵声良颁发了聘书。
延伸阅读:“为敦煌而读书”的赵声良
一位55岁的云南昭通汉子,今年5月5日,正式成为敦煌研究院的第五代掌门。
敦煌,甘肃酒泉市代管的县级市,作为一个行政区划的意义,早已被作为全球著名人类文明遗迹的意义所掩盖。
而人员规模达一千多的敦煌研究院,也绝不只是一家研究机构,还是与故宫博物院等量齐观的国家一级博物馆,负责敦煌地区所有石窟文物和艺术的保护、管理及整个景区运营,还设有中国壁画研究基地、中国古代壁画保护工程中心等全国性专业机构,连布达拉宫壁画的修复重任,也由敦煌研究院承担。

(赵声良院长讲解敦煌艺术)
随着任前公示期结束,2019年5月5日,当代著名学者赵声良走马上任,担任敦煌研究院院长,并同时任院党委副书记。而由其一手策划、主导,得以来到云南的《穿越千年的永恒》敦煌艺术展,此时,仍在呈贡大学城云南大学图书馆举行。
此前,赵声良任敦煌研究院党委委员、副院长及学术委员会主任。第三个头衔,常常在相关媒体报道中被忽略,在我看来,这才是最为核心和重要的。也正是由于在当代中国、乃至世界敦煌学领域的突出贡献和巨大影响,他才成为了新一代敦煌研究院掌门。
在这个于赵声良本人、于敦煌而言都注定是一个新起点的日子里,赵院长千头万绪,忙得脚不沾地。我发微信问:有何感想,有何新举措?
良久,他答:呵呵,亚历山大。
即便被开除,也要“为敦煌而读书”

(敦煌壁画 陈大衡摄影)
曾经,赵声良承受着极可能被敦煌研究院开除的挣扎与痛苦,日以继夜,寝食难安。1996,作为敦煌研究院《敦煌研究》学术期刊编辑,32岁的赵声良获得公派机会,赴日本进修。两年期满后,他想留下,自费攻读美术史硕士、博士。
“院领导非常爱才,可能是怕我不回单位,对此并不支持,甚至非常生气,听说准备把我开除。”他首度面对媒体开口,对我谈起了这段不为人知的往事。
那是赵声良第一次走出国门,第一次与当时敦煌研究处于世界最前列的日本学者和同行们接触。他实在不愿意,自己刚刚洞开的视野,就此戛然而止。之前,在参加由本单位主办的多次关于敦煌的学术活动时,他早就强烈意识到了国内学者视野普遍的封闭与狭窄,不但敦煌研究落后于别人,对于敦煌学在国际上的发展以及世界其他石窟艺术的情况,更是一无所知。

(敦煌壁画 陈大衡摄影)

(敦煌壁画 陈大衡摄影)
“所以,即便被开除,我也要读书。我留在日本是为了敦煌学,我是为了敦煌而读书!”多年以后,说这话的时候,55岁的赵声良依然热血沸腾。
为了承担高昂的生活和学习费用,开始自费读研的赵声良,不得不到餐厅端盘子、洗碗、扫地,到印刷作坊当印刷工。“本来学习任务就极其繁重,打工又筋疲力尽,还经常要去参加日本关于敦煌的各种学术活动,拜访相关专家。最要命的是,还随时担心被院里开除。说实话,好几次,我几乎都坚持不下去了。”
后来,这位来自中国贫困地区云南的小个子所爆发出的强大“内力”,赢得了日本导师和许多专家的认可,也赢得了大额奖学金。他被推荐到当地报纸当中文编辑,到培训学校教中文,还给一家博物馆承担中文解说词和资料翻译,收入情况极大改观。
就这样,在日本整整7年后,赵声良拿到了美术史博士学位。
再苦再难,也不敌敦煌艺术的震撼
日本求学归来,赵声良的人生和事业拨云见日,就此豁然开朗。
还在日期间,新上任的樊锦诗院长为了“拴住”这位学术新秀,已将其增选为院学术委员会委员。2003年回来后,又任命其为《敦煌研究》编辑部主任,实际负责这本权威的敦煌学刊物。“领导过我的好几任院长,每一位都是我的贵人,他们做人做学问的风范,都深深感染着我。”陷入回忆,赵声良憨厚的娃娃脸上写满感恩。
1964年8月,赵声良生于昭通。20岁即从北京师范大学中文系毕业,并立即背起行囊,从北京坐上了开往甘肃敦煌的火车。从小,他就非常喜欢画画,看过一些关于敦煌的作品和资料,理想,便在胸中暗暗滋长。大三时,他偶然看到时任敦煌研究院院长段文杰在《中国青年报》的采访中感叹敦煌人才青黄不接,便深受触动。
“父亲觉得大西北条件太艰苦,写了三四十封信劝我回云南。我也是怕回去后有所动摇,就干脆直接去了敦煌。”赵声良说。

(敦煌文创产品 陈大衡摄影)
上世纪八十年代的大西北是多么的荒凉与艰苦,满怀理想而来的赵声良终于有了深刻的体会。
当时,他和另外一个同样新来的年轻人一起,被安排住进莫高窟洞窟外的一处破旧小平房。冬天晚上零下十几度,火炉子不能熄,也不能有明火,他们不会“捂”,常常半夜醒来冷得像冰棍一般浑身僵硬。老鼠也多,多次爬到头上,钻进被窝。
“食堂的菜很辣,我吃不了,干脆买个馒头,就着西瓜,经常这样就对付一天。最难受的还是喝水问题,那时整个敦煌人都是喝大泉河碱含量超重的水,我一喝就拉肚子,几乎天天拉。熬了大概两年,才渐渐适应。”
然而,一切难以想象的困难,在敦煌艺术给予赵声良的巨大震撼面前,都不值一提。“太兴奋了,每天每时每刻,只要进石窟面对那些美轮美奂的壁画,就都会沉浸在强烈的兴奋和震撼中!”
成为第五任敦煌掌门,致敬四代前辈
“面对敦煌,谁可能不被深深震撼?”在云南大学《穿越千年的永恒》敦煌艺术展开幕式现场,赵声良一边讲解着所展出数字高清壁画的历史文化内涵,一边多次发出如此感叹。身为“敦煌人”的荣光与骄傲之情,溢于言表。
赵声良说,敦煌石窟群的建造过程,从四世纪至十四世纪,绵延约千年,石窟中海量般遗存下来的各种壁画,镌刻着我国古代千年来的美术发展史。同时,各个时代的其它艺术门类发展和整个社会生活的风貌,也无不记录其中。尤为重要的则是,由于位于丝绸之路的咽喉要冲,敦煌壁画也较为完整地呈现出了千年以来中西方文明的碰撞与交融,因此,在无以伦比的艺术价值外,还具有极其重要的历史和文化价值。

(在《穿越千年的永恒》展现场,赵声良院长激情讲解敦煌艺术)
“能将敦煌艺术带回我的家乡云南,非常开心。我希望,以后这个展览还能陆续进入更多的云南学校,让家乡父老尤其是年轻人,更多地了解人类瑰宝敦煌。”赵声良说,“美育就是要享受古代的艺术,普及传统文化就是要看敦煌。”
在敦煌研究院,赵声良主要从事敦煌艺术与中国美术史研究,出版《敦煌石窟艺术》、《敦煌石窟全集·山水画卷》、《敦煌壁画风景研究》、《艺苑瑰宝——敦煌壁画与彩塑》、《飞天艺术——从印度到中国》、《敦煌石窟艺术简史》等大量著作。其中,《敦煌石窟艺术简史》(2015年,中国青年出版社)还被评委年度“中国好书”,为敦煌艺术的推广和普及,做出了十分突出的贡献。
“上世纪八十年代就有一个断言:敦煌在中国,敦煌学在国外。这种尴尬局面,如今是否还存在?”
在赵声良看来,这早已不是问题。这是好几代敦煌“掌门人”、无数“敦煌人”以及全国、全世界热爱敦煌的人共同努力和关心的结果。
他说,必须郑重地向历任敦煌研究院院长致敬——
常书鸿(1904-1994),1943年创立敦煌艺术研究所(敦煌研究院前身),并任所长;
段文杰(1917-2011),第二任院长,1984年上任,至1998年;
樊锦诗,第三任,1998年4月至2014年;
王旭东,第四任,2014年12月,至2019年4月。
4月25日传出消息,历史的接力棒传递到了赵声良手中:因故宫博物院“明星院长”“网红院长”、著名学者单霁翔退休,王旭东赴京接掌故宫,任副院长已三年的赵声良,拟升任敦煌研究院院长、党委副书记。
5月5日,作为敦煌研究院第五任掌门,赵声良正式履新。
赵声良,1964年8月出生,中共党员,云南昭通人,在职研究生学历,文学博士,研究馆员。赵声良1984年大学毕业后即进入敦煌研究院工作,2016年3月任敦煌研究院副院长。敦煌研究院官网显示,赵声良主要从事敦煌艺术与中国美术史研究。
文图:昭通广播电视台记者耿昭汝
部分资料来源:@昭通日报 @微昭通 温星入滇记 文图/温星
编审:陈大衡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