帕男:灵魂被赤裸是尴尬的,所以那些被揭穿灵魂的诗人必须死。诗人的生命只存在于诗歌的秘密间,而不是那个密码被解密之后的尴尬时刻。每个诗人都是斯芬克斯的人面狮身的女妖。当她的谜语被猜中,无数个斯芬克斯就从巍峨的峭崖上跳下去摔死了……
编者按:随着移动互联网时代的到来,诗歌在一定层面已经进入了当下精神生活的核心;同时,中国诗歌网的不断发展和壮大,也让越来越多的实力诗人渗透到了中国诗歌网的各大板块!正值中国新诗走过百年之际,为了展示中国实力诗人的气质和风彩,我们有了这次独家策划,对中国实力诗人进行系列访谈!
实力诗人访谈之帕男
诗人

(在报社任主编的时候)
帕男,原名吴玉华,瑶族,湖南永州人,现居云南楚雄。中国作家协会会员,中国少数民族学会会员,楚雄州文联专职副主席、云南省报告文学学会副会长、云南省网络作家协会副主席、《金沙江文艺》常务副社长、常务副主编、《37度诗刊》总编辑。著有诗集、散文集、长卷散文、长篇报告文学、报告文学集《男性高原》《落叶与鸟》《帕男诗选》《落花,正是一个旧时代的禅让》《只有水不需要剃度》《在云南在》《等我驾到》《第37只兽的阵亡》《一抹秋红》《俚语湘南》《生态云南记》等三十余部。《帕男诗选》获第十九届鲁黎诗歌奖、第十九届柔刚诗歌奖提名奖。2015年获首届“中国城市文学”诗歌奖。《大冲刺》《大道同行》《新庄记事》《绝飨》获中国作协、云南省委宣传部、云南省作家协会文学创作重点项目。
简评

(年轻时候帕男)
初读帕男诗歌,我几乎为他诗中那种逻辑思辨的自我挣扎而窒息,而读不下去,对于诗中那一种跳跃的解构思维和自我矛盾,这是一种想迅速逃离的感觉与欲望。但我答应好友要写一篇关于帕男诗歌的赏析文字,所以平息了情绪的两天之后,我又读了第二遍第三遍,到今天我读了不下十遍后,不免又对他诗歌多元化的内涵延伸,和别具一格的逻辑思辨性,心生深深敬意。
作为解构主义的代表,帕男诗歌,很显然打破了常人的思维和诗歌架构。无论是诗歌内容,还是语言,都让人觉得耳目一新。他的这十首诗,乍读,感觉矛盾,混乱,就像两个小人在打架,即一种内心深处强烈的自我博弈。但正是透过这独特的哲学思辨,才引发我们关于文化、社会和人生的深刻思考。

(陪莫言楚雄采风)
以第一首“我拿米喂养骨头”为例。通常我们认为瓷质的碗,很容易碎烂,是脆弱的,而骨头是坚硬的,是刚强不屈的。但诗人在这首诗里,起句却说“碗还不是最脆弱的是骨头”,这很让人惊奇,何以他能得出这样的结论?接下来他说“只要和斤重挂起钩来明码标价那肯定/每块骨头都会/趋之若鹜”,让你懂得,哦,原来他是针对那些在利益面前丧失气节的社会丑恶现象有感而发。但又如何解决这个问题呢?诗的第二节和第三节,诗人提出“打断骨头作为教训”这个历来的做法,和“放弃骨头不可能”坚定的回答。历来做法不可取,放弃骨头又不可能,那怎么办才好呢?诗人最后给出了答案“要不像对待一只碗那样/我拿米喂养”,也回到诗眼上来。现实生活颇多艰辛和无常,我们有时不得不放弃一些东西,比如名利,比如得失,但我们不能放弃“骨头”,我们不能放弃我们对社会的责任和良知,不能放弃我们做人的节操。“米”是我们生命之源,所以诗人要拿“米”来“喂养骨头”,用生命来喂养一个民族的脊梁和希望。这首诗的内容具有思辨性的,短短三节,却结论,推演,再结论,收放自如。这首诗语言无疑是新颖的,且富有想象力的。同样语言新奇不落俗套的,还有他的第五首“装在画框里的故乡”。诗人不写故乡,而画故乡,不说故乡回不去的无奈,而说”再点缀些狗吠篱笆疏影我不敢说这就是故乡/倒更像败笔/拟声太难了”。相框中的故乡,其实是记忆里的故乡标本了,只能靠怀念来想象。这一份失去故乡的疼,会深深打动每一位游子的心。诗人潜意识里在呼唤环保,给故乡以自然、安宁、祥和。
关于帕男诗歌的逻辑思辨哲学性,几乎每首诗中都能见到。再看第四首“一只乌鸦的死,是相对的”。常人眼里的乌鸦,因为它黑色的羽毛,沙哑的啼鸣,是一种不祥的鸟,一种不待见的鸟。但诗人在这一首诗里,将对乌鸦的片面误解,和对“春天”、“故人”、“窗外”的类比中,逐层推演,得出结论“乌鸦的黑,依然是最诚恳的”,乌鸦的黑,是纯粹的真实,没有任何虚饰的成分。他不想在春天见到一只乌鸦“被搁浅”,他不想人们因为乌鸦的外表偏见,而忽略了乌鸦的智慧和乌鸦懂得反哺的内在美。还有第六首“我灌输给唢呐的青铜时代”对金色诱惑的思辨,对唢呐孤独的思考,第七首“特定时间”,十四个“反而”的反复出现,也让诗人复杂又痛苦的思辨历程,清晰可见。
——绿茶一盏(诗坛小人物)

(接见演员)
阅读帕男诗歌,需要厘清其思想内蕴及文化背景的特殊选择,初步了解后现代哲学、美学、社会学、伦理学理论观念,思维方式,把握世界的方式。还要有时时克服迥异的观念形态、社会历史形态造成的观察、分析问题的思路、方法、手段不同带来的矛盾的足够心理准备,否则,阅读其作品往往不得其解,不得要领,造成对诗歌文本的误读误判,得出与实际不相符的结论与判断。
——柳韵荷姿(诗坛小人物)

(在印度访问)
诗人可以天马行空地驰骋想象,也可以敏感地对任何事物作出自己最原始状态的回应,但是,想,终究只是想的,到底还要落脚于现实,千万不要以情感的带入式作为宣泄、解脱,使得自己深陷其中,无法自拔。而敏感的好处就在于发现,继而呈现,这是诗人之笔,也是诗人之所需。因此,当想象与敏感发生碰撞甚至是产生连锁反应,对诗人来说,无疑是一场暴风雨的序幕正在拉开。
读帕男的诗歌,无论是从语感,节奏,还是造境上来说,都带有自己独特的鲜明的个性符号。读完这十首诗,我甚至大胆的认为,帕男的多数诗歌都是口语与书面语的一种对质和反抗,用词用句的反口语化,阅读程序中的反意识化,思维变换中的反情绪化,在一定程度上都是对其诗歌自身的一种细致考量。但是在这个考量之外,我们还应看到的是,作者对人、情、事、物、虚无等特质的处理,更像是基于一种自我意识为主导的反大众化、反平庸化。如果抛开这些问题,仅从作者这十首诗歌说开,我想,褒贬不一,应该是一个较为准确又略显模糊的评价与心理定位。
我在读的过程中,心里总会有那么一个梗,从头至尾都伴随着我,提示甚至是警醒着我,不要被他所带跑,带偏,可我的心告诉我,如果不试着从跑偏的过程中探出个究竟,那我还有继续读下去的理由吗?我想,答案应该是肯定的。正因为我在作者的陷阱中、圈套里不断的进行解构重组,我才能够对其表达出完整的异议来,才能在赴死的过程中体验生的可贵与脆弱。帕男是我目前阅读范围内的一个异类,从我第一次读这十首诗开始,我就在心里这么暗暗的对其下了定义。当然,这似乎也是我第一次阅读帕男的诗歌,网络世界如此之大,能够静下心来,细心阅读一个诗人的作品,想来也是一种可怜的奢望。
——柳鹤鸣(诗坛小人物)
(1)总体来说,伟大的诗人首先是一个具有特别重要现实批判意义的诗人,然后才是主观领域的诗人身份的认证。也就是说,伟大的诗人既是唯物辩证法也是历史唯物主义的代言人。尽管帕男在自己的诗歌创作过程中兼顾了历史或现实意义的思考方针,但是,他所有这些关于历史或者说现实主义的讨论的目的,仅仅只是证明历史上所发生的一切历史世界的价值包括对现代生活的影响,没有看出现代社会本身所具备的前进力量。他只主观的认可是历史的力量形成了今天发展的动力,这种思考实际上是一种否定人后来力量的反动学说。或者说,他仇视时间的流动,他只希望时间能固定在某一固定的区间而不再流动。这种仇视时间的心理我们可以追溯到他父亲死亡留给他心理活心灵的创伤。他没有能够见上父亲最后一面的遗憾促使他潜意识当中将所有时间停留在他父亲还活着的那个时间。这种唯心主义的愿望是他始终在根本上谴责唯物主义的主要内部环境。这种心理导致他后来的诗歌创作中,由一个无信仰者转变为唯心主义的教徒和唯心主义诗歌书写的实践者。
在他从事三十年的诗歌创作过程中,他有过许多与其他著名诗人合作的机会,但是由于他始终不愿放弃关于批判时间的思考,所以使他又一次放弃了站在巨人肩上而成为伟大诗人的机遇。我们在对他的采访中曾经专门提到过这方面的问题,他只是简单的说,我的诗歌要靠自己的努力。这种独立的创作心里曾经被一些诗歌评论家描述为特立独行的状况。这种独立的创作信念,实际上我们可以理解为某种意义的孤立而不是真正意义的独立。这种孤立在表层来看,似乎是离伟大诗人的距离越来越遥远,可是实际上,他成为伟大诗人的可能性从来没有消失过。他是独一无二的创作方针,或许是具有特别重要的先导意义,但是这需要时间和历史的验证。他是一个具有能力的诗人,可是这种能力却引导他成为孤立或专制意志的诗人。他曾经自羽为自己是美国自白派的忠实信徒,但是实际上他从来没有进行过真正的关于自我和现实主义的自白思考。

(在孟加拉国访问)
(2)没有人能够打倒帕男的诗歌主张和严谨的思考方针,这个能够打倒他的对手不是别人,恰恰是他自己。他一生中由于坚持的是一个将历史与现实空间互为参照互为对应的书写方针,这使他错过成为伟大诗人的机会。我们在观察帕男诗歌特征的时候,总能非常明显的可以看出他首先是一个农民,然后才是一个诗人的存在。因此,在他的诗歌中首先没有被表现出来的就是那么一种属于现代文明及其现代生活或者说是现代群体所热衷于欣赏并接受的娱乐元素。娱乐元素的匮乏,无形间给帕男诗歌的推广造成了出乎意料的灾难性后果。他总是喜欢在历史的深处去寻找人类社会思考及其思想变革的痕迹。尤其是善于在对历史的表述中强化着自己主观的思考。如果他能够真正从一个农民诗人的角度出发,去书写农民历史的痕迹,他或许可能成为一名出色的农民诗人。但是,他毕竟不是一个纯粹的农民。
与此同时,在他还没有走出那个瑶族山寨的时候,他那个富有文化,戏曲或者说民族风情的家庭就使他完全在身上几乎完全消除了那些真正的农民基因。实际上,他是个社会身份非常丰富非常复杂的农民。但又不是纯粹意义上的新型农民。因为他几乎没有参加过具体的农民生活实践就已经在心理上与农民的身份完全分离。在他长期的外出谋生的经历中,所体现的既有一帆风顺的方面,也有贵人相助的宿命方面。尤其是在他历尽磨难在云南定居之后,多层次文化在他思想内部的介入,是使一个诗人无法找到地域身份的关键所在。一方面,他试图体现着一个关于湖南出生地的故乡情感,然而又不能在良心上背离在现在给他生存条件的云南。这种非常复杂的矛盾情绪,是导致他最终无法书写真正感人乡情的主要因素。
严格来说,一个人只有一个出生地,这首先是必须肯定的东西。出生地的独立性及其独一无二性,决定着某种程度的排他性的存在。因此,这个环节的存在,是帕男一生怀念故乡的主要情绪。因此,帕男所有对于故乡的赞美与赞颂其实都是站在第三方区间思考的结果。这其实是个怀念大于赞美的故乡情感。实际上到现在为止,他对出生地的情感一直是保持在一个别梦依稀的状态。在帕男书写故乡情感的诗歌时,其实他已经关注到这个方面的存在。在他2013年创作的《当故乡变成一个虚词》的时候,所表现与寄托的情感既有对背井离乡的检讨,也有试图在潜意识当中识别故乡的弥补情绪。当然,他对云南也是非常感恩的。他曾经吃住在云南的农村,为那里的经济建设,文化建设,文明建设作出过卓有成效的努力和付出。可是,这种成功的社会实践在后来的诗歌创作过程中并没有理想的表达出来。这些社会实践应该成为帕男后来诗歌创作中的某种程度的指导方针及其指导思想,以使他书写出一些能够代表现实主义的诗歌作品。
 (与佤族儿童一起)
(与佤族儿童一起)
实际上这对于帕男的诗歌书写是个非常遗憾的忽略与放弃。在某种程度上,这种在农村生活的经历实际上也是一种非理性的流浪与流放的形式,可惜的是他没有能够抓住这个机遇在诗歌中淋漓尽致的表达中国新时期农村的建设脚步和精神轨迹。实际上在后来,帕男尽管非常怀念这一流放的经历,但是却始终没有以比较高度的方针融如自己的诗歌创作。这一宝贵流放体验的放弃,实际上促使帕男的诗歌创作方针在距离一个农民或社会实践的诗人之路上越走越远。由于在他后来的生活当中几乎是以某种领导意义的身份生活在现实当中,于是在他的诗歌创作过程中所在诗歌中采取的书写态度是,他既无法体验真正的民间生活,也无力从平民的角度去书写一些真正属于民间疾苦的生存之思考,因此,在他后来的诗歌创作中,他无法用娴熟的笔法去描写他所生存的社会和时代。他几乎陷于的绝境是,借助于自己潜意识当中已知的社会事件去抒发自己的主观思考,并且是几乎不自觉的将上帝引入自己的诗歌创作之中。
——苗洪(非著名评论家)
访谈

(在文体局工作的时候)
中国诗歌网:我知道你曾经是一个媒体人,一个诗人,后来做了行政领导,在写作上又是一个徘徊于多个区间的文学工作者。抑或行政领导、是诗人,散文作家,报告文学作家,其中的任意一个角色都需要你成为而不是扮演,尤其作为诗人的时候,其它的身份会否成为你的旁骛?
帕男:除了诗人的身份,所有的身份都是职业、谋生工具。只有当自己是诗人的时候,才是最纯粹、最干净的。写诗是自语方式,对灵魂、神鬼、天地万物的直接对话。
诗歌是诗人辐射的电磁波,诗人可能更多的只顾及到辐射,而忽略了对电磁波的介绍、解析。诗歌是诗人自我意识形态的构建,是设计出的谜语。
读诗的人就是射电望远镜。
中国诗歌网:我了解,你从事诗歌创作30余年,这漫长的时间里是否经历过了厌倦,甚至是挣扎?你对自己取得的诗歌成果满意吗?
帕男:我首先对自己诗歌创作作个自评:基本满意。我只把写作纯粹地当作爱好,和有的爱好没有什么两样,有的喜欢钓鱼,有喜欢打麻将,有喜欢喝酒,有喜欢吹拉弹唱,等等。我没有为自己的写作设定一个目标,更不会趋迎特定形态,但不马虎、不蝇营狗苟。将近30年是一个时间概念,真正投入诗歌创作前前后后也就10来年,再说,创作是有感而发,而非时时刻刻。
姑且以35年的时间计算,我先后出版了12种读本,包括了《男性高原》《落叶与鸟》《帕男诗选》《落花,是一个旧时代的禅让》《只有水不需剃度》《等我驾到》《我在云南在》《罪例》《第三十七只兽的阵亡》等。
我自诩小地方写作的人,但诗歌格局并没有受所处地理位置的影响,而是睁大眼睛,视野向外,兼容并包,取长补短。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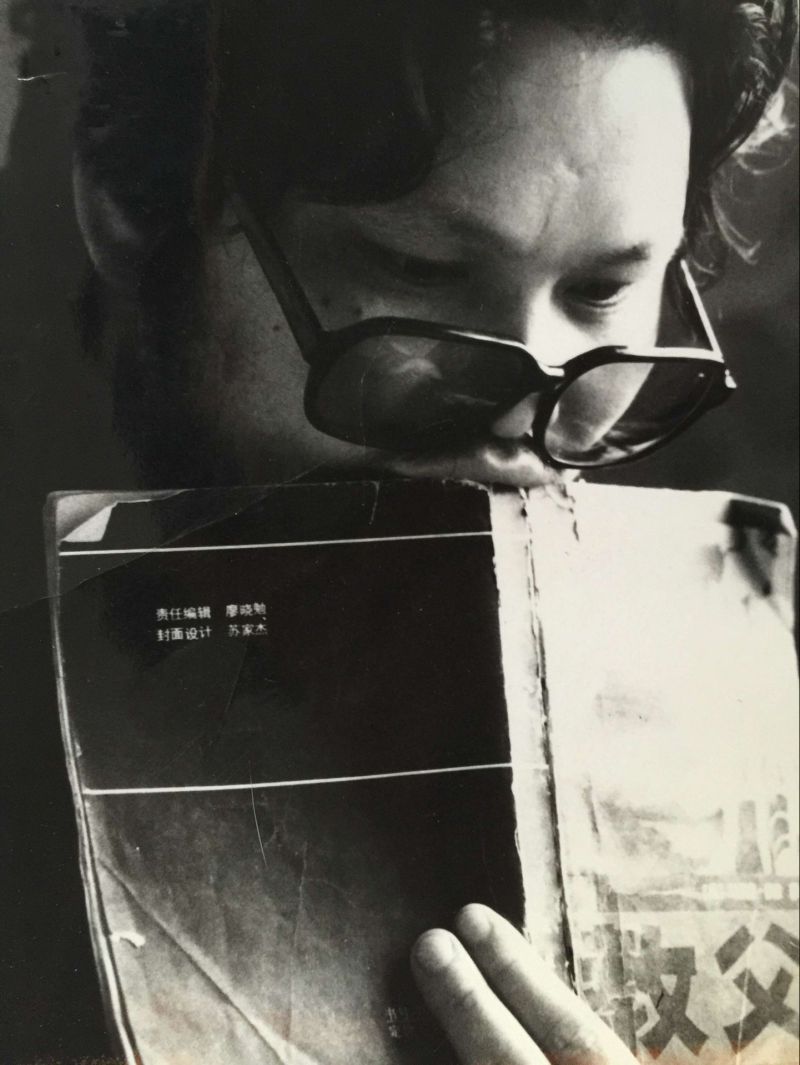
(当记者时候的帕男)
中国诗歌网:《在云南在》是否潜在着你的乡愁?因为我知道你是湖南人,但大学毕业不久就到了云南工作,乡愁是是诗人的良药还是毒药?
帕男:著名评论家张柠说过这样的一句话:现代文明的背景下,流亡状态非常普遍。可以是精神的流亡,也可以是语言的流亡。他还有一种返回的冲动,这一点上跟怀乡病很相似。这不妨碍他的心不断地回去,也不妨碍他的梦,在梦里不断地回去。
如果说现代人类的生存必须与流浪紧密联系的话,那么这么由生存需求所导致的精神流亡既是一个关于生存危机的思考,也是一个关于精神危机的控诉。当这种关于精神危机感的控诉被来自现实主义的思考所控制时,你就必然要承认这种精神危机感的合法性。如果一个诗人仅仅把流亡的意义解释为一种精神的宣泄及释放,那么这种释放背后所隐藏的情绪就是一种关于生存的无奈。当然,在考虑现代文明之下的这种流亡情感时,我们还要考虑到一个比较重要的区间就是,他或许是以憎恨的情绪对待他的流放之地抑或是怀着歌颂的热情去投入他的第二故乡。如果一个诗人不热爱他现在的生存之地,那么他就无法以谨慎的客观的态度去审视第二故乡的现实状况包括时代的价值观念及其道德观念或者说其他更加广义的社会议题。
《在云南在》是我在云南处境下辐射出的“电磁波”。
一年前曾经有学者采访我如何从地域上划分自己的身份归属地。关于这一点,我似乎是从来没有去认真的考虑过,也没有对于自己身份的归属进行过一些必有的求证。从自身而言,我出生湖南永州,严格来说其属于一个真正意义上的民族写作者。为了生活及其诗歌的创作,我一生辗转全国各地。湖南,湖北,广东,海南等地都曾有我流落与奔波的足迹。我最终落地云南,是自己的选择也是组织的需要。我深爱着云南这片美丽却贫瘠的土地。我的生活及其创作都与云南这片边陲的土地融为一体。
云南是我的第二故乡。在我的诗歌创作中有机的将云南文化及其政治,经济、人文、民族风情引入自己的作品之中。除了《在云南在》,我的《云南方言》《我在西部靠南》《人民大理》《留守儿童》及其《女巫》等作品都深度融入了云南的传统意义包括现代意义的各种不同类型的地域性特别明显的诗歌元素。

(在大理闲适)
中国诗歌网:我知道你办了一份《37℃诗刊》,不置可否纸质刊物,纯粹地讲纯文学刊物都办得十分不容易,可谓处境艰窘,那你为何还要办这样的刊物?
帕男:当然无功利可言,如选择今办刊物无异于自掘坟墓。
这不是危言耸听,一份官办刊物,一两千份的“发行量”,还觉得沾沾自喜。不在这个圈子的人,也一样觉得,上一篇文章就像金榜题名,自慰的心理可以想见。
催生《37度诗刊》我愿意看成是“飞蛾扑火”,真的。从有此动念开始,我就没有想过《37度诗刊》永生永世。这是不客观的,我更愿意走一步看一步,走到哪里算哪里,正所谓“只求曾经拥有”,“昙花一现”也未必不是记忆,也未必不可以刻骨铭心。
于是便有了《37度诗刊》首次诗会:在楚雄师范学院图书馆,来自大理、玉溪、昆明、楚雄多地的诗人和大学教授、大学生的际会,大家纯粹得只有读诗一个念想。吃饭、住宿等等都被抛到脑后。
紧接着是端午节的“望苍山,向洱海大理诗会:先祥云,后大理,一波三折。被莫须有的戴上了“非法集会”帽子,福兮祸所伏,祸兮福所倚,“非法”反而助推了《37度诗刊》,使这份还在襁褓中的诗刊“一夜成名”。
“望苍山,向洱海”名副其实,读诗地点选择在洱海湿地公园,整个诗会以天设缔造的大自然为舞台,读出了《37度诗刊》气度、视野和情怀。参加诗会者,不无流连忘返。
再后来又举办的《37度诗刊》帕男读诗会,这是多形式的必然要求。个人读诗会不但开创了“我爱我诗”的新局面,而且直接证明了“无功利可言”命题的成立。
帕男读诗会借中国书画院彝人古镇创作基地,一次诗书画的绝美结合,诗歌如添两翼。
有人问,我如此这般,为了什么?
我答:只为了生命的意义!

(在香港)
中国诗歌网:《37℃诗刊》创办5年来,外界有何评价?
帕男:当今诗歌刊物众多,但以质量求生存是诗歌刊物的唯一出路。《37度诗刊》也不例外。我们虽然强调包容,但是并不意味着对所有诗歌作者给予“安慰”。而且每份刊物都有自己的定位和选稿标准,《37度诗刊》不欢迎滥竽充数的诗歌,尤其一“啊”到底和唾沫横飞的口水诗人,虽然我们不能给作者支付微薄的稿酬,但我们可以保证,如果你的作品能上《37度诗刊》,其本身就是一种莫大的荣耀。 比如首刊出版发行后,《北京文学》编辑部主任张颐说的: “看到《37℃诗刊》让我很吃惊,一个小地方的诗刊,却有那么宽广的视野,少有。我以为小地方的刊物,都是发表本地的几个诗人的作品,而《37℃诗刊》发的作品不但全国,还有海外诗人的作品。这个确实很震惊” 。
《凤凰网》读书频道主编严彬:“《37℃诗刊》刊登的诗歌很好,像本期推出了90后一个彝族小女孩的诗歌,她的诗歌写得很棒,很好。”这不但是对《37℃诗刊》的褒扬,也是对上刊诗歌作者的嘉奖。
中国诗歌网:在苗洪的评论中,我看到了他将你定义为某诗歌流派的代表人物,你认同他的定义吗?你是如何看待诗歌流派的?你想拥有自己的独门独派?
帕男:我查过字典,流派指水的支流,另指学术、文化艺术等方面有独特风格的派别。流派不是说出来,是做出来的,首先我是一个诗人,一个勤勤恳恳的诗人。现代诗歌诞生以来,诗派林立是事实,从20世纪初的尝试派到当下的第三神性写作,在众多的流派中,我没有“站队”的想法,首先写诗要由著自己,借鉴但不模仿,我的诗歌就是我的诗歌。想有自己的流派不当真,不过我特别提倡诗歌要有“场所精神”,并致力于将诗歌的“场所精神”发扬光大。

(在泰国访问)
中国诗歌网:我看过你的一篇访谈文章,你极力地提倡诗歌必须具有“场所精神”,它是借建筑学的“场所精神”吗?如果是,那诗歌的“场所精神”和建筑学上的“场所精神”有什么异同?
帕男:是借用了建筑学上的“场所精神”。“场所精神”是著名挪威城市建筑学家诺伯舒兹(CHRISTIANNORBERG-SCHULZ)在1979年提出了来的概念。“场所”在某种意义上,是一个人记忆的一种物体化和空间化。也就是城市学家所谓的“SENSEOFPLACE”,或可以解释为“对一个地方的认同感和归属感”。有人说,建筑设计是人类爱与恨、欲望与梦想在大地上的投影,通过人性的尺度,寻求有著人文内涵,人文价值的空间场所精神。诗歌的“场所精神”恰恰相反,是将物体和空间变成一个人的记忆。

(在武定万德农村)
中国诗歌网:你能否谈谈诗歌“场所精神”的理论支撑是什么?
帕男:理论来自于实践。首先要申明的,我的诗歌创作并非在我要宣导诗歌的“场所精神”之后,只是写著写著就悟到了“场所精神”对于诗歌的重要性。
诺伯舒兹在他的《场所精神——迈向建筑现象学》这本书中提到了在很早古罗马时代,罗马人就认识到了“场所精神”的重要,在他们是意识里,所有独立的本体,包括人与场所,都有其“守护神灵”陪伴其一生,同时也决定其特性和本质。
我以前看过刘宇扬发表在《深圳商报》上一篇文章,题目就叫做《场所精神》,他谈了一些很好的观点:比如他说:“地面的材料,一堵墙的质感、顏色,一排房子的高低,一座山的形,水的声音,一阵风的味道,甚至一道阳光的强弱,都是构成‘场所精神’的整体性特质的综合元素。”
刘宇扬还谈到了“场所”和“艺术”的关係。他说:“所谓艺术的具体化指的是由创造思考转为创造物品或创造行为的一个实践。换句话说,不论这艺术品本身是幅写实画,或是座抽象雕塑,乃至于当代流行的行为艺术,都是一种具体產生的物品或事件。而这些事与物,便成为解释、表达、或包容人们生活中的矛盾和复杂的一个媒介。”对于这点,诺伯舒兹提出了这样的说明:“当人们将世界具体化而形成建筑物时,人们开始定居。具体化则是艺术创造本身的一个体现,而这与科学的抽象化正好相反。”
刘宇扬还谈到了:“艺术作品,经由其介于作者本身和宇宙之间的表现,帮助人们认定‘场所’”。

(主持诗会)
德国存在主义哲学大师海德格尔(MARTINHEIDEG GER)说过:“诗人并非是个不食人间烟火的代表。相反的,诗人把人们带入世界,使人们更属于这个地方,进而在此定居。生活上的诗意,也因而使人生具有意义。”诗人当然要食人间烟火,诗人们把具象的物体、空间、现象用文字以诗歌的方式表达,即对存在的一切意象化,诗人是这个世界的一份子,不管是亲历者还是围观者,诗人都可以通过意境的创造来体现诗歌的场所精神,但诗歌的本质还是“存在”,使其“精神”存在于诗化了的“场所”里面,意象表现出场所感。简而言之,就是把房子造的有诗意,营造一种“诗意栖居”的意境,把诗歌写得更像场所,可以触摸。亦如海德格尔认同“自我”存在的自明性,认为自我不需要被排除或悬置。海德格尔称“自我”为“此在”,这个“此在”是一个被拋入存在中的“此在”。以“此在”为中心,通过“此在”的观察、活动,体验等等,成就了“此在”于存在中的生存方式。这些就是诗歌“场所精神”的理论支撑。
中国诗歌网:“诗歌的场所精神”的代表人物是谁?是你吗?还是以你为主的一群人?
帕男:我当然是代表人物之一啦(笑)。之所以称之为“之一”,那说明还有“之二”、“之三”或更多。体现出强烈“场所精神”的诗歌很多,不胜枚举,比如诗人东皮、瑶山人、媛斕篓、杨天孩、木芷等等,也许就只有帕男,因为我一厢情愿地喜欢这些诗人的作品,尤其是表现出的强烈的“场所精神”。
中国诗歌网:你高举的“场所精神”诗歌写作,是否是“场所精神”空壳下功利写作,更不客气的讲就是“口号党”,是博取眼球的一个噱头?如果真是“场所精神”的忠于者,那这杆旗帜又能打多久?
帕男:写诗是为功利、作秀或自我标榜为什么什么,那就不要写诗了。流派不是拉山头,也不是依靠行政手段就可以划分,更不是为争地盘纠集起来的乌合之众。首先这些诗人的结合是体认上的相同,是以“场所精神”为纽带,甚至彼此间尚未谋面的一个诗歌群体。其次如果流派是被给予的,那只能像一块招牌,说不准哪天风一吹,牌子就掉了,徒有虚名或浪得虚名都不是真的诗人。
我们循守的“场所精神”是自然而然地,它是维系我们诗歌创作的动力源,只有坚守“场所精神”的高地,才可以让我们诗歌走得更远。
我还想多说几句,场所精神说宣导的正切合我们这些诗人的存在状态。这个群体中,都有一个共同点,就是“流浪”。流浪是灵魂在流浪,诗人始终保持著看风景的心理状态,不管是物质上的苦苦挣扎,还是精神上的痛不欲生,但最终都能超越,都能以诗歌为依归,始终不渝地存在著,并活跃在诗坛。

(业余一把摄像)
中国诗歌网:你怎么评价“场所精神”诗人群体创作水准,更残酷的话,把你们拿到现实中国诗坛作比较,本来就寂灭诗歌现状,能有多大作为?
帕男:请不要比较,写诗不是刻意而为,也不可能竞技比赛那样定下一个可以比较的标准。
“场所精神”诗人群体的存在,仅仅是为自己的诗歌存在,让诗歌说话,这也就够了。
“本来就寂灭诗歌现状,能有多大作为?”
诗歌寂灭,这也是不客观的,开场锣鼓看似热闹,但好戏一定是在后头,我打这样的比喻,这与政治、文化、经济、社会等等背景有关,所谓的寂灭,实际上沉淀,是流水以湖的形式存在。
“场所精神”诗人群体的作为要看是不是历史的适者,适者生存的法则谁都懂,诗人不是靠信誓旦旦,而是靠作品说话。作品的生命力就是实实在在的作为。

来源 中国诗歌网
责编 刘榕杉
审核 邱忠文


